2005年,台灣銀行逐步規劃標售山仔后的美軍宿舍群,激起了在地居民的反感,民間人士組成山仔后文史工作室,多方奔走,一方面尋求社會大眾的認同與聯署,一方面向政府部門尋求機會,以阻止台銀將這片宿舍賣給財團和建商。因為這4.2萬多坪的土地如果被開發為別墅、大樓,除了會破壞山仔后的大環境,造成缺水、汙染、交通擁擠等問題外,深具歷史價值的美軍宿舍群也會被剷除,消失。
經過這批民間人士的努力,台北市文化局在2008年公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為「歷史建築」,這暫時阻止了台銀標售宿舍的活動,留給民眾認識這片建築的機會。筆者正是其中受惠者,有幸能在歷史建築中,找尋藏在台灣各個角落中所暗藏的故事。我認為美軍宿舍的未來,不是台灣銀行能擅自決定的。因為這片建築群具有深厚的歷史意義,它見證了台灣冷戰時期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,同時還承載著一種獨特的,因兩種文化交織在一起所產生的生活經驗。如果僅為少數人的利益,將他改建為住宅,那麼在文化上肯定是個沉痛的損失。我們應該要了解自己的歷史,盡可能維護、記憶自己的過去,這片建築是相當好的一個教材。
而要了解這片美軍宿舍群的文化價值,必須掌握附著在它上面的歷史與生活經驗。筆者很幸運地訪問到一位董姓女士,曾於1963年至1975年之間擔任美軍幫傭,十二年來她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山仔后各區的美軍宿舍,還包含山仔后周圍的菁山路、天母中山北路上零星的美軍住家。本文希望從她的經驗、記憶著手,描寫這片宿舍背後活生生的情感,和確實存在於這片土地上的故事。筆者一方面希望這段獨特的歷史不被遺忘,同時也希望這些記憶和情感,能賦予古蹟一種新的生命,展現它的文化價值。
在理解山仔后美軍宿舍群時,我們必須有一個基本認知:美軍宿舍是按軍階分區的,每一個區域都有不同的生活樣貌。現存的C-1、C-2、F、H-1、H-2等區,除了房舍風格各有差異外,當年也分別住著不同軍階的軍官。當然,每一區都有其獨特的生活經驗,本文將就每一區美軍宿舍,分別「放上」屬於它的故事,再搭配董女士的其他記憶,刻畫這片宿舍的歷史。
古蹟背後的記憶—山仔后美軍宿舍幫傭的故事(吳承瑾)
首先簡單介紹董女士背景。她出生於1949年,母親也在美軍宿舍中擔任幫傭。由於董女士的母親已經去世,所以只能從董女士身上打聽當年幫傭的記憶。她小學畢業後就開始工作,在1960年代,美軍幫傭的酬勞相對優渥許多,於是董女士和就在擔任幫傭的母親,學習幫傭的工作內容,同時自己去找美軍家庭簽約。老實講在那個日子苦哈哈的年代裡,董女士並沒有甚麼充裕的時間閒待在家裡,去慢慢摸索英文會話和西餐的做法,她必須迅速學會這一切,然後投入職場賺錢貼補家用。當時她和媽媽各作各的,第一次幫傭是在十三歲。董女士回憶她從媽媽那裏學會部份工作內容,舉凡西餐的做法、漿洗熨燙軍服技巧、到日常英語會話等,但絕大部分還是得自己摸著做,而且要學得快才能保住工作。幫傭的薪水相當優渥,她20歲時月薪8000多台幣。董女士26歲進入美軍顧問團總部會計處上班,擔任「視察員」(sales auditor),偶爾還須視察全省的美軍宿舍,包含台中清泉崗、台南、高雄左營等地方,這時已經是1970年代了。這12年來她幫傭過的家庭,範圍遍及山仔后A~F區、外加菁山路和天母的零星地區。美軍兩年到三年一調,通常幫傭會做到該雇主調走。
 美軍家庭會雇用幾種人幫忙做家務,一種是幫傭,專門處理室內的事物,舉凡三餐、洗衣服、打掃房子、照顧幼兒等,都是幫傭的職責。還有一種叫「yard boy」,或也有人叫「car boy」,這種是專門處理事外事務的,例如修剪草坪、矮樹籬笆,洗車等工作。幫傭必須每天到雇主家上班,但yard boy只要三到五天,甚至一星期去一次就行了。幫傭一定雇用女性來擔任,而yard boy則顧名思義,一定是男性。另外許多美軍也願意多花錢,多請幾個人到家分工服務,例如專門的廚師或褓母,有時也會有男性,叫做「house boy」。當年美軍顧問團可以說為山仔后創造了很大的就業市場,許多居民,甚至文化大學的學生(洗車之類的零工為主),都曾擔任過幫傭或yard boy,董女士的父親也擔任過yard boy,不過他也已經去世了。
美軍家庭會雇用幾種人幫忙做家務,一種是幫傭,專門處理室內的事物,舉凡三餐、洗衣服、打掃房子、照顧幼兒等,都是幫傭的職責。還有一種叫「yard boy」,或也有人叫「car boy」,這種是專門處理事外事務的,例如修剪草坪、矮樹籬笆,洗車等工作。幫傭必須每天到雇主家上班,但yard boy只要三到五天,甚至一星期去一次就行了。幫傭一定雇用女性來擔任,而yard boy則顧名思義,一定是男性。另外許多美軍也願意多花錢,多請幾個人到家分工服務,例如專門的廚師或褓母,有時也會有男性,叫做「house boy」。當年美軍顧問團可以說為山仔后創造了很大的就業市場,許多居民,甚至文化大學的學生(洗車之類的零工為主),都曾擔任過幫傭或yard boy,董女士的父親也擔任過yard boy,不過他也已經去世了。
在美軍口中,幫傭不叫maid,而為她們取了一個相當本土化的名字—「ama」。當美軍雇主向他人介紹自家幫傭時,他們會說:「This is my ama.」。是的,這個詞就是從閩南語的祖母來的,但是在美軍的用法裡,它比較接近「大嬸」、「女士」這個意思,而和祖母有相當程度的差異,也許最早的一批幫傭本來就有點年紀,叫阿嬤就對了。董女士一開始當幫傭時,十四歲的她也被稱作ama,但是後來取了一個英文名字,Jenny。年輕一輩的幫傭多半會取英文名字,平常幫傭之間也是用英文名字稱呼,有時甚至不知道對方原來的中文名字。而老一輩的幫傭,例如董女士的母親,就沒有取英文名字,一直被稱為ama。
這間天主堂坐落於華岡路和愛富二街交會處,當年這裡屬於F區,這裡曾經是美軍軍官做禮拜的場所。據天主堂的神父說,最早的禮拜堂很小,坐不下那麼多人,而這個地段又屬於禁止開發的地區。最後是在美軍顧問團透過外交部的交涉下,才取得開發這一塊地的權限,也因此有了這間禮拜堂。當時美軍顧問團只負責出資,設計和建造的工作完全交給教會方面。我們可以輕易地看出這座天主堂融合中西文化的現象,金黃色的琉璃瓦和中國式的屋頂,還有門口兩隻石獅造型的陶塑像,當你走近它時,這種感覺是相當有趣的。神父回憶當年的情形,他說當時早上八點是中文彌撒,九點則是英文彌撒。美軍軍官是很具親和力的,他記得當初有一位中將在彌撒時,親自拿著奉獻籃。
 右側四連張圖呈現的是位於F區的愛富二街,「愛富」這個名字就是來自「F」,在1960年代這條路更窄,同時也沒有高聳的空心水泥磚牆。美式住宅,僅僅使用矮樹作籬笆,隔出公私領域的分界,家宅四周,往往有大片的草坪。根據董女士的印象,這些空心磚牆、車庫屋頂都是在台銀出租宿舍給台灣人後才改建的。如今這些房屋的結構依舊相當穩固,在現代樓房之間,這條街顯得既神祕又獨特,一幢幢瓦片、白牆的洋房,令人感覺彷彿置身另一個國家。F區當初是配給校級和尉級的軍官,房舍在所有宿舍種類中,面積較大,也擁有較大片的草坪。
右側四連張圖呈現的是位於F區的愛富二街,「愛富」這個名字就是來自「F」,在1960年代這條路更窄,同時也沒有高聳的空心水泥磚牆。美式住宅,僅僅使用矮樹作籬笆,隔出公私領域的分界,家宅四周,往往有大片的草坪。根據董女士的印象,這些空心磚牆、車庫屋頂都是在台銀出租宿舍給台灣人後才改建的。如今這些房屋的結構依舊相當穩固,在現代樓房之間,這條街顯得既神祕又獨特,一幢幢瓦片、白牆的洋房,令人感覺彷彿置身另一個國家。F區當初是配給校級和尉級的軍官,房舍在所有宿舍種類中,面積較大,也擁有較大片的草坪。
 左側照片是H-2區,當初是配給將級軍官的宿舍,房舍為獨棟,面積較大,草坪也維護得較為完整。根據董女士的說法,高階軍官年紀較大,通常不會攜家帶眷,所以不需要處理帶小孩的工作,三餐的量自然也較少。但是這些位於C-2、F、H-2區的房房舍相對大得多,打掃整理很花力氣。例如窗帘、窗台、所有家具每天都要擦拭清理,基本上把整棟屋子清掃一遍就要花掉大半天,而最累人的是軍官對服裝要求很高,漿洗軍服對幫傭而言是大工程。董女士說燙軍服是門學問,洗好剛上漿的衣服,曬乾後像塊木板一樣硬,要用噴霧器微微噴濕,然後用布包起來稍待片刻,等衣服軟化後再一部分一部分熨平,一套軍服往往要燙上一個半小時,燙好後可以立在地上。這些大大小小的瑣事可以讓人忙上一整天,但還是有休息的片刻,這時各家的幫傭會互相串門子,當然大多是住在山仔后的人。
左側照片是H-2區,當初是配給將級軍官的宿舍,房舍為獨棟,面積較大,草坪也維護得較為完整。根據董女士的說法,高階軍官年紀較大,通常不會攜家帶眷,所以不需要處理帶小孩的工作,三餐的量自然也較少。但是這些位於C-2、F、H-2區的房房舍相對大得多,打掃整理很花力氣。例如窗帘、窗台、所有家具每天都要擦拭清理,基本上把整棟屋子清掃一遍就要花掉大半天,而最累人的是軍官對服裝要求很高,漿洗軍服對幫傭而言是大工程。董女士說燙軍服是門學問,洗好剛上漿的衣服,曬乾後像塊木板一樣硬,要用噴霧器微微噴濕,然後用布包起來稍待片刻,等衣服軟化後再一部分一部分熨平,一套軍服往往要燙上一個半小時,燙好後可以立在地上。這些大大小小的瑣事可以讓人忙上一整天,但還是有休息的片刻,這時各家的幫傭會互相串門子,當然大多是住在山仔后的人。
在H-1和H-2兩區中間,筆者找到幾棟式樣不同於該二區的洋房(下兩張圖),並不在台北市文化局劃定的「現存」美軍宿舍區塊中。這幾棟房舍面積較小,應該之前是配給較低階軍官的宿舍。如同上面第二張照片,這幾棟房舍隔著空心水泥磚牆,和公寓樓房並立著。
董女士說這是屬於E區的,也就是大部分被拆除,改建為台銀員工訓練所的E區宿舍中,碩果僅存的幾棟房舍。早期E區和H區的邊界是犬牙交錯的,所以時過境遷就變成現在的分布方式。E區是配給尉級軍官和士官的。董女士對這一區印象非常深刻,因為她十五歲時曾經接下一家沒有人願意接的美軍家庭,就在這一區。為什麼沒有幫傭要接呢?因為他們全家共有十一人,除了大人以外,小孩各個年齡層都有,最小的還不會走路。這可真是場硬仗,她還記得當時一天的工作流程。
每天早上七點,幫傭就到美軍家上班了,首先準備全家的早餐和午餐。美軍通常在工作處有自己吃飯的地方,但美軍太太就要幫忙準備午飯了。(美軍太太一般會兼職,不過也有一些是不工作的)。在大人上班、小孩搭戴著午餐盒搭上校車離開後,幫傭便開始打掃房屋、洗衣服、照顧幼兒,就這樣忙到晚上。下午校車將小孩載回家,美國小學生是沒有作業的,這時通常就出門去玩。晚上大人回家,幫傭則一直到忙到晚餐結束、洗好碗才回家,這時大約是晚上七八點。這是一般的狀況,美軍軍官時常有別的活動,例如看電影、打保齡球、參加舞會等,這種情況下幫傭必須看家,直到主人回來,這樣回家時間常常就在半夜十二點以後了。董女士的母親就常常半夜一兩點回家,稍稍睡一下後,四點又起來洗自家人的衣服,然後出門,趕在七點到美軍家上班。
 左側是C-1區,當年是配給校級和尉級軍官的宿舍。C-1區荒廢得相當嚴重,在中美斷交後這裡似乎沒有被台銀出租。不過這裡也是改建最少的一區,我們還可以看到當年的木造結構,只不過大部分的房舍都被台銀圍了起來,外人只能從雜草的縫隙中,一窺這些陳舊的房舍。
左側是C-1區,當年是配給校級和尉級軍官的宿舍。C-1區荒廢得相當嚴重,在中美斷交後這裡似乎沒有被台銀出租。不過這裡也是改建最少的一區,我們還可以看到當年的木造結構,只不過大部分的房舍都被台銀圍了起來,外人只能從雜草的縫隙中,一窺這些陳舊的房舍。
關於C-1區其實有個很有趣的傳聞,董女士說這區當年盛傳鬧鬼。董女士當年他在這區服務時,照顧過還不會走路的幼兒,她記得晚上明明就把小孩抱到嬰兒床上去睡了,忙了一會兒卻發現嬰兒躺在客廳沙發上。她說半夜碰到這種事還真是令人毛骨悚然。鬧鬼的傳聞,導因應該是C-1區的建地本來是一大片的公墓,台灣銀行當年徵收土地時,才將部分墳墓遷到了稍遠的菁山路附近。C-1區西南邊其實還緊臨了一片公墓。在台灣民眾的觀念中,「驚動」死者本來就是個禁忌。但對美國人來說,基本外交禮儀做到後是不會太在乎這些忌諱的。對美國小孩來說,這些死者更不是需要恐懼的對象,董女士的母親曾經看過美國小孩把死人的大腿骨,撿來當鼓棒敲著玩。不用多說,這對老太太而言簡直是天大的冒犯。我相信類似的文化衝擊必定時常發生在幫傭間,那鬧鬼這種流言蜚語會那麼普遍,其實是其來有自的,我們應該可以把這看作是幫傭面對文化衝擊時,一種心態的展現。
 相較於C-1區的殘破,C-2區顯得光鮮亮麗多了(右側圖),這裡比C-1區晚建,格局也較大、較開闊。今天走在C-2區,仍然會有走在另一個國度的感覺,然而透過高度僅齊肩的圍牆,台灣人的花圃、房舍就矗立在對面,近在咫尺。兩種世界就這樣擠在小小的山仔后裡,交織出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。
相較於C-1區的殘破,C-2區顯得光鮮亮麗多了(右側圖),這裡比C-1區晚建,格局也較大、較開闊。今天走在C-2區,仍然會有走在另一個國度的感覺,然而透過高度僅齊肩的圍牆,台灣人的花圃、房舍就矗立在對面,近在咫尺。兩種世界就這樣擠在小小的山仔后裡,交織出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。
下左圖可以看見突出在房屋主體外的浴室,洗澡水是用戶外的爐子用煤球燒的,當然在有熱水器的現在,這些設施已不復見。下右圖可以看見門口的庭院,不過車庫的棚架是台灣人裝上去的。
每逢節日,幫傭都要準備應景的食物,董女士在這十二年間,學會做復活節的烤火雞、南瓜派,幫傭平常也常常烤餅乾等西點,有時董女士在家也會和媽媽一起烤餅乾。幫傭做久了,她們在家家常常煮西餐,台式料理的技術反而不怎麼樣。每次做西餐,家中長輩就會臭著臉。董女士手邊還保存了許多餅乾配方,和西餐的食譜,當年這些食譜常常在各家幫傭間流傳著,可以說是工作手冊一樣的東西。即使過了這麼多年,烤派、烤餅乾的香味她仍然記憶猶新,那是一種很溫暖、美好的氣味。董女士家裡還曾經向美軍購買二手的瓦斯爐,那是上面四個爐,下面附烤箱的那種。
烤火雞、牛排這類食物,美軍會在晚餐時,切下一部分包好送給幫傭,這種做法,會讓人覺得雇主和幫傭之間,除了契約關係以外,還有一種家人般的情感,我覺得這在研究這段歷史時,不能忽略的一點。帶回家的食物是很「熱門」的,董女士的弟弟開玩笑說當年他們家只吃得起蘋果,因為買不起其他水果;只吃得起牛排、火雞排,因為買不起豬肉。當然董女士的祖父母是不吃牛肉的,前提是不要有人告訴他們這是牛肉。董女士的弟弟說他們小孩子都知道這點,所以要說這是牛肉,這樣就能多吃一點。不過祖父母的臉色想必是很不好看的。
法律規定幫傭每星期有一定休假日數,每家不同,而且偶爾會改變休假天。對幫傭而言這等於少拿一天薪水,因此假日幫傭會彷彿大風吹一般,互相交換服務家庭,以零時工的方式繼續工作,這是領鐘點費的。
美軍顧問團在總部附近有間專用大賣場,販賣美國軍人需要的日常用品。由於免稅,價格較便宜。幫傭有時會託請美軍幫忙購買某些東西,例如蘋果(美軍自己買蘋果時也會送幾個給幫傭),但是因為美軍的消費額是有限制的,所以機會不多。買回來的東西,例如蘋果,大多是自家吃,常常一顆蘋果切成八塊,分給祖孫三代嘗。有時也會偷偷賣給附近雜貨店,但是這種黑市有風險,所以次數也不多。
 不只幫傭會過美國節日,美軍在過年時也會應景一下。左圖的一美元硬幣,是當年美軍送給董女士家人的壓歲錢,幾十年來這個硬幣被當成特別的紀念品,見證了那個和美國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。
不只幫傭會過美國節日,美軍在過年時也會應景一下。左圖的一美元硬幣,是當年美軍送給董女士家人的壓歲錢,幾十年來這個硬幣被當成特別的紀念品,見證了那個和美國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。
僅僅一位幫傭,就能提供這麼多珍貴的資料,見證這段冷戰時期生活的歷史。這是活生生的,台灣和美國的互動經驗,也是台灣在美國圍堵政策下,其扮演國際角色。然而筆者只寫出了一半的記憶,另一半在美軍軍官,以及他們家屬身上。我們如果能找回這些美軍的記憶,兩相搭配後,一定能賦予這些建築物一種新的意義,更完整的述說五十年前台灣如何面對國際,以及國際如何面對台灣,山仔后的每一棟美軍宿舍,背後都承載了這樣的生命力,不只是陳舊的建築,而是歷史的見證。但是這些見證人,正凋零中,筆者訪談時就這點感到十分無奈與可惜。我們其實應該趁早訪問在地居民,保留當年第一手的記憶,這點急迫性不下於保護建築物。
同時這片美軍宿舍,也需要民間、學術單位共同維護,無論是建築、土木、城鄉、攝影、環境、歷史等學科,相信都能在這片宿舍群中,找到充實自己,回饋社會的方法。我們需要這種教育方式,記憶與反省,而不是在一味地在拼經濟的潮流中,破壞了古蹟,遺忘了歷史,毀壞了文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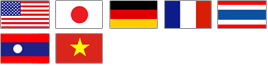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1 comment
阿歷茲 says:
十月 29, 2012
何不聊聊輕鬆一些的話題?
當年,許多學生租居在宿舍群中,所以,發生在其中的青澀愛情故事不少,要是護育聯盟舉辦徵文、號召一下,可能會收來熱烈回響,引起大家對宿舍群的注目呢!